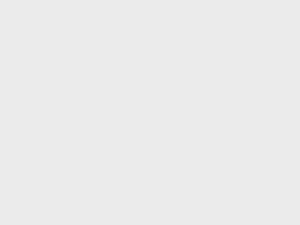- A+
宋朝的朋党之争直接导致了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宋朝的朋党之争是怎样影响士风和政风的?
封建社会,士大夫为争权夺利,在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就叫朋党之争。朋党问题虽不始于宋代,却是宋代政治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朋党之祸成为宋代政治生态最为突出的现象和内容。

宋朝的朋党之争,真正的白热化时代,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当时的北宋王朝,虽说表面繁荣,其实却已不堪重负。国家财政连年赤字,行政效率低下,朝堂上冗官扎堆,国防危机四伏,已经是不改不行的地步。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一群老臣们,却只知道给新皇帝宋神宗唱高调。这才叫年轻的宋神宗忍无可忍,慨然启用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北宋变法上马!
然而,随着变法的开始,北宋的朋党之争,也迅速的高涨起来,早年唱高调的司马光一伙,摇身变成了反对变法的顽固派,与王安石麾下的变法派玩命死掐。虽然在后来的史书里,各类史家对司马光等人的作为极力美化,把他们的折腾看做为国为民的正义行动。但无奈司马光的铁杆盟友文彦博,一句话暴露了这群人的最恶劣用心: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所谓的富国强兵,在这群人看来,统统就是浮云,动了自家“士大夫”的利益,哪怕毁了大宋王朝的前途,也要组团跟变法玩命。北宋朋党之争的真实目的,就是这样恶劣!
于是,在北宋顶着反对派压力,朋党之争的口水声里,坚持了十五年变法后,眼看着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北宋王朝,却因为宋神宗的病故横遭转折,彻底掌握大权的司马光顽固派,几乎是电闪雷鸣的手段,把已经取得成效的新法统统废除。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为了彻底踩倒变法派,号称忠君爱国的司马光,竟连大宋国家尊严都不顾,在北宋已经掌握对西夏战争主动权的好形势下,主动谄媚示好,将北宋将士浴血收复的西夏六寨割给西夏!
也正是在这群旧党的折腾下,北宋的政治空气迅速恶化,王安石生前得力干将,北宋变法的旗帜人物蔡确,更被他们罗织罪名害死。而这桩血仇,也导致宋哲宗亲政后,继承王安石蔡确变法遗志的变法派干将章惇,在这场朋党之争中,掀起了对旧党们最惨烈的报复:大批旧党官员被株连论罪,已经去世的司马光被追夺一切赏赐册封。就连支持司马光的高太后,都险些在死后被废掉尊位。北宋朋党之争,就这样一步步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
当然必须称道的是,虽然变法派对守旧派,在宋哲宗年间开始了惨烈的报复。可是对于守旧派的政治主动,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却是去粗取精,尽力吸纳,绝不干司马光这样的龌龊事。也正因这个胸怀,才有了宋哲宗晚期,北宋一度攻克横山地区的辉煌武功!
但随着宋哲宗去世,旧党推举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上台,北宋彻底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正是这样一种你死我活的朋党之争,最终也毁掉了北宋的政治根基,整个官场变成了逆淘汰。到了宋徽宗年间,朝堂上更变成了奸人蠢人扎堆,最终上演靖康之耻。明朝好些学者,把司马光看做北宋灭亡的罪人,正是因为这朋党祸国的道理。
宋代朋党之争是怎样影响士风和政风的?
《宋史·文苑传》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这段文字说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来和深远影响。后人也常盛赞宋朝文治超越汉唐,社会长期安定繁荣,并对尚文政策的奠基者宋太祖、宋太宗给予很高评价。
宋仁宗是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他将祖宗兴科举、重文教的政策推向新的高度。仁宗在位期间,朝廷多士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基本构成了宋仁宗亲政后官僚队伍的中坚力量,这批人登上政治舞台,可视为宋代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士大夫力量重新崛起、主体意识再度觉醒的一个标志。
这些人锐气十足,在学术渊源、文章风格、禀性气质和从政作风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特点:因为初出茅庐,他们在政治上较少顾忌;又因多供职于台谏、馆阁,故每每自视清流,自诩为朝廷正气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奋不顾身的行为特征。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提倡正统,崇尚名节,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人主的意志面前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当内忧外患日趋严重时,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以这批人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为开端,宋代一贯的“右文”政策从此才具有了实质性意义:士大夫作为饱受人文教育而有志于仕途的阶层,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既是王朝合法性的解释者,又是辅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和礼法之治的实践者。在强邻环峙的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有助于增强正统国家观念、文化统一性和凝聚力。宋朝利用文化传统的优越地位,与强邻作持久抗衡。宋真宗时,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即已表现出这种冲动,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这对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在这种背景下,士大夫在政治实践中标榜恢复先王之道和贤人政治,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和君主负责的同时,也要注重民本,关心民瘼,甚至倡言“民贵君轻”,提倡为政以德,强调官员自律。宋代许多名臣巨子都曾阐述礼义廉耻、忠孝气节对澄清官场风气、指导官员行为的重要作用。杨万里说:“用宽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然后法可尽行,赃可尽禁也。”岳飞的名言更是震烁古今:“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这些思想和言论对于净化官吏头脑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朋党成为宋代政治突出现象
然而,也正是从宋仁宗时期起,官僚集团中的朋党之争日益盛行。朋党问题虽不始于宋代,却是宋代政治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朋党之祸成为宋代政治生态最为突出的现象和内容。
在历史上,“朋党”从来都不是一个褒义词。它起初指同类之人为了私自的目的而互相勾结,后引申为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例如,《战国策·赵策二》载苏秦之语曰:“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晋书·郄诜传》云:“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新唐书·李绛传》更直截了当地说:“趋利之人,常为朋比,同其私也。”在历代人心目中,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无道义可言。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对统治者来说,朋党现象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由于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可怕武器。
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崛起,宋仁宗年间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先是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继而演化为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代被视为朋党者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欧阳修曾撰《朋党论》一文,认为朋党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他们在政争中不避嫌疑,以“君子之党”自居,甚至以朋党为荣。
欧阳修等人的努力非但未能为朋党正名,反而造成严重后果。首先,他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者,皆为朋党。其次,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也为人们所熟知,统治者更是以防范臣下结党营私作为维护皇权的首要任务。面对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论点显然缺乏说服力。最后,他把臣僚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并奏请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改革者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派感到不安,产生动摇。
新进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也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突出表现为: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结果授人以柄,也招来人主的猜忌;始则以朋党自任,终则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敌我不分,虽一心想铲除小人,却易为小人所误。彼等虽夙志以天下为己任,却也为其仕宦生涯设下重重障碍,最终难以有所作为。
这些弊端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对立双方都无法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遂使这些论争重新陷入“义利之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思维窠臼,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又使得统治集团陷入无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争斗之中,最终成为新政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熙宁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并蜕化变质为党派倾轧和纯粹的利益斗争。所谓新党,往往打着维护新法的旗号,干的却是排斥异己的勾当。旧党内部亦复如此。政坛风气愈益恶化,野心家、阴谋家趁机专权乱政,吏治腐败、贪污横行的局面难以遏阻。
官场恶斗又从反面教育了士大夫。他们心灰意冷,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完全丧失了往日的锐气。那些还没有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也群起效仿,亦步亦趋,失去进取心和正义感,读书只是为了做官,做官只是为了趋利。陆九渊说:“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尽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在这种意识驱使下,文人士大夫所读之书皆场屋之书,所习之术皆求官之术。所谓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都成了幌子,无人潜心深究。这就造成了宋代文风极盛而士风日坏的弊病。
同时,宋代科举制度中“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弊端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考试内容日趋狭窄僵化。绍兴年间还允许“通用古今诸儒之说,及出己意”。到理宗朝时,经义考试遂以朱熹《四书集注》等为标准答案。由于考试内容十分狭窄,为区分成绩高低,考官规定了种种固定程序加以限制,如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等,开启明清时期八股取士的先河。由此,士大夫中有真才实学者日见其少,皓首穷经、只为稻粱谋者比比皆是。自诩清流、空言心性者充斥朝野,而在治国理政方面则乏善可陈,甚至懵懂无知,造成“吏强官弱”的局面,为胥吏上下其手、营私舞弊打开方便之门,官吏沆瀣一气、合伙作恶。
尽管宋代朋党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曾经超越权与利之争,并被视为士大夫自我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实践和运用,但就其实际结果来看,并未开辟全新的政治局面。相反,它对政坛和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严重干扰政务的正常运行和革新的顺利推进,进而演化成党派倾轧和恶斗,成为令人诟病的痼疾。正如王夫之所言:“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自命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术以相禁制。妖气所薰,无物不靡,岂徒政之所繇乱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风斩焉。斯亦有心者所可为之痛哭矣”!